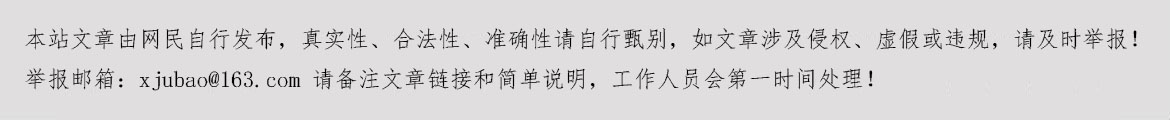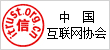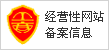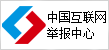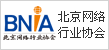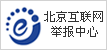优拓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商旅生涯、教育科研、体育健康、国际资讯、综艺娱乐、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我不爱看自己视频聊天时的样子”
2021-11-16 11:08:35
帝国时代2 下载 https://www.aoe520.com/aoexz/
你身份证上的照片好看吗?自拍的时候你要开镜像吗?听自己的录音会不会尴尬到脚趾抠地?……我们看到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我们,总是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道鸿沟的存在,就会有各种丢人现眼的尴尬时刻。
对日常生活中的尴尬过于敏感,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比起那些迟钝的人,做一个意识得到尴尬的人,或许会让我们用别人的视角填补自我认知的空白。所以,那些让我们忧虑的尴尬谈话,可能往往物有所值。
01
“我不爱看自己视频聊天时的样子”
我想起了几年前一种被称为“视频通话整容”的新兴整形手术项目。2010 年左右,这是一个网络编辑和电视新闻制作人都无法抗拒的“热门话题”。我是很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我与这两种人都密切合作过。
到2012年春天,华盛顿特区的整形外科医生罗伯特·西加尔博士估计,在他每年见到的约100个要求整容的来访者中,有差不多1/4的人是因为厌恶自己在视频通话中的样子才走进他的办公室的。“他们会说,‘我不爱看自己视频聊天时的样子’,”他在描述这种手术的视频中说,“‘我的脖子看起来又粗又肥。’”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忧,西加尔设计出了新的手术方法,类似于标准的颈部提拉手术,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手术的切口是在耳朵后面,而不是在下巴下面,这意味着疤痕会被隐藏在你的视频聊天对象看不到的位置。西加尔说,视频通话的问题在于,它就像一面“类固醇上的镜子”。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想了解自己。我们记录自己行走的步数;我们痴迷于记录极其详尽的子弹笔记;我们花69美元来测试自己的DNA;我们对新闻网站上的性格小测验嗤之以鼻,却还是老实作答。对了,我的性格更像《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弥桑黛,你的测试结果是哪位女士呢?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自知只能看到有限的自己。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心理学家菲利普·罗查特称之为“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个词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但它描述的那种感觉不是——想想那些被我们认为“令人尴尬”的情景: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一张自己的丑照;向老板要求升职。在这些情况下,你认为你所呈现给世界的样子被迫与现实世界看到的你的样子狭路相逢。
你本不在意你的声音,直到你听到自己的录音;你觉得自己挺好看,直到一张你自己毫无吸引力的照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你自认为是一个领导者,但你的老板仍然当你是初级职员。这些情景让你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尤其是当别人对你的看法赶不上你的自我评价时。
以视频通话为例,几十年来,视频通话一直被认为是科技领域的“下一个热门事件”,但普及速度却远远没跟上许多专家的预测。专家们预言这项技术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贝尔实验室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推出了当时技术最尖端的视频通话服务—可视电话。6年后,贝尔在匹兹堡的8家公司里安装了38台这样的设备,这样一个开端还算是说得过去,但贝尔对视频通话设备有着宏伟的计划:他展望,到1975年全美国将有10万台处于应用状态的设备,到1980 年将达到100万台。
期望虽高,可视电话却彻底失败了,原因有几个,成本是其中之一。在1964 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一通视频通话每分钟收费27 美元,约合今天200 美元。在公司总部,工程师罗伯特·拉齐是为数不多的在办公桌上安装了可视电话的人之一,但他只接到过老板阿诺·彭齐亚斯的来电。“我觉得它很令人尴尬,”拉齐这样描述这台设备,“因为我不得不盯着他看。”40年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历史学家谢尔顿·霍克海瑟也表达了与拉齐相似的观点。他猜测这款电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并不能完全确定人们愿意在电话上被人盯着看”。
几十年后,像FaceTime这样的新一代视频聊天应用也让人体会到了同样的不适感。根据谷歌最近的一项调查,大约1/6的美国人说他们避免使用视频聊天应用,因为它让人觉得“无礼”。你应该往哪里看?看镜头,也就是看向对方的“眼睛”?还是看屏幕上对方真正的眼睛(这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看旁边而不是在看他/ 她本人)?还有,难道就没有人会因为对方的脸撑满了屏幕而感到厌恶吗?那样就好像你俩隔着令人不自在的仅仅10英寸(约25cm)亲密距离面面相觑。
此外,人们对自己在视频聊天中的样子非常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或许觉得“视频聊天整容手术”听起来很极端,那么要知道,从《华尔街日报》到《悦己》杂志等众多出版物都发表过针对视频通话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一些如何在视频聊天中显得更有吸引力的非手术建议。有那么一阵子,似乎FaceTime在2010年秋天随着iPhone 4一同问世,验证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无尽的玩笑》一书中关于“视频压力”的预言。这种压力“还有可能变得更糟,你可能会变得过分虚荣,如果你特别在意自己的脸面,也就是其他人眼中你的外表的话。而且不开玩笑地说,谁会不在意呢?”
02
“我”与别人眼中的“我”
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许多年前,菲利普·罗查特乘地铁时,一群年轻女士带着一沓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上了车,那些照片是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拍下的。她们聚成一团,越过彼此的肩膀翻看那些照片时,“在车厢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他在2009年出版的《心念他人》一书中如此回忆道。当某位女士看到一张有损自己形象的照片时,就会将它一把夺走,试图不让朋友们看到。某个年龄段的读者可能会由此回想起,这就是“脸书”出现之前你要求朋友去掉他们给你贴上的标签的方式。罗查特是埃默里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关注自我意识,所以那天在地铁上,他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着那群人的滑稽动作。
“这些女士的行为固然很顽皮,”他后来写道,“但那种行为背后的力量和紧张是非常强大的。”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年轻女性看到自认为的丑照时尖叫抢夺的样子似乎令他觉得有趣,但文中也格外强调了,她们的行为启发他联想到了自己目前正在思考的理论:“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和他的母亲聊起她最近接受的白内障手术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突然看清了周围的世界。”他在电话里用令人愉快的瑞士法语口音对我说,“她在恐慌中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路过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样子,她完全被吓坏了。”她现在可以看到,她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得多。罗查特自己现在也已经60多岁了,他了解这种感觉。他告诉我,年纪越大,越会觉得自己比在镜子中看到的人年轻得多。
接着说我和罗查特那段关于衰老的谈话。关于他的母亲,他告诉我:“她正在面对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内心深处的感觉,以及外表投射出的形象。”一些研究尴尬的心理学家把这叫作“生命自我”和“肉体自我”之间的区别:前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后者出现在现实世界里。你可以假装这两个自我是一体的,是相同的,直到某种令人难堪的晦气事情发生,把你从那个幻想中猛然拉出来。你脚下拌蒜,让自己跌倒,或是撞上了一扇极其干净的玻璃门,你忽然间意识到自己的样子肯定非常可笑,而那个在外面招摇过市的你并不总是能达到你在想象中给自己设立的标准。
这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定是世界看待你的方式,这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的深刻一课。你的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你的看法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其他人的交往——这本该是一件自然的,甚至是有趣的事情——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安。你想让他们看到你眼中的自己,或者至少是你当下想要表现出的自己,而把那个版本的自己呈现给对方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德詹尼丝讲过一个与此有关的笑话,说的是有时候人们会在脚下发生磕绊之后,索性莫名其妙地慢跑起来,就好像在对所有看到那一幕的人说,哦,我本来就打算跑步的。
在同一期节目中,德詹尼丝还简要地探讨了另一种已经被我们大多数人内化为习惯的对磕绊和跌倒的处理方式:即使你真的伤到了自己,也没关系。你强忍痛苦,一笑而过。毫无疑问,身体上的疼痛较为直接,但社交上的痛苦有时候会更加强烈,持续的时间也可能更久。几年前的某个清晨6点钟,我在东河的林荫道上跑步时遇到了我那位喜欢早起的朋友玛丽。我自认不具备成为早起者的生理特质,但有时候我喜欢表现得像是一个爱早起的人,就在那一天,我的伪装让我自食其果:我们才慢跑了大约10 步,我就径直撞上了一根路灯柱。
我知道!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能想到,我疼得要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右大腿承受了主要的冲击力,回到家后,我看到了一团狰狞的紫色瘀伤。然而,在那一刻,我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笑了起来,站起来继续跑。“我没事。”我记得我这么骗玛丽,“不,真的,我没事。有事我会说的。”
才不会呢,有事我也不会告诉她,而且我打赌你也不会。这是我们在彼此面前做戏的一个小例子。想想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观点:社会是一座舞台。那天在东河林荫道上跟玛丽在一起时,我假装自己没事,就这样把她从鸿沟的对岸邀请到了我这边。在这边,我们继续前进,假装那个令人吃惊的笨拙时刻不曾存在。在每次像这样的一场小小表演中,我们都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上仓促地建造起桥梁。
除了试图以某种特定方式展现自己,我们还在努力解读他人尝试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那个语气是怎么回事?我们执迷于这些细微线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想要弄清楚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另一方面是为了监控对方是否乐于接受我们想要塑造出的形象。由于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之间的差距,这往往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努力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
罗查特告诉我,“我们努力调和,就像是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戈夫曼把这称为“信息游戏”。有时为了引导别人来到鸿沟彼岸,在自己所在的这一侧,我们会故意做一些细微的事情。比如,在衣着上花些心思:你小心翼翼地歪戴帽子,或者故意只把衬衫的一侧塞进裤腰。你也可能把这样的心思运用到发短信之类的事情中:你可以关闭智能手机的自动更正功能,以保持全文小写的优雅美感。但我们还是有可能无意间发出一些关于自己的非文字信号,比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语调。
要想成功避免尴尬,你必须接受我正在创造的情景,并以之为依据对待我,而我也必须为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和即兴演出的基本规则差不多:是的,而且(yes,and)。即兴演出的演员们都会接受演出搭档所呈现的任何现实,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有人以扮演校车司机开创一幕场景,只有喜欢出风头的傻子才会跳出来说什么“不,这是一艘火箭飞船。你是一个外星人。我们正朝着月亮前进”!同样的道理,当我说了我很好,即便你刚刚看着我一头撞上灯柱,你也要顺着我的话说—如果你不想让气氛变得奇怪的话。
03
“比起那些迟钝的人,
我宁愿做一个意识得到尴尬的人”
当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表现出的自我被证明与现实不符,而且这种不符无法用善意的谎言抚平,尴尬感便油然而生。在专门提供单词或者词组的“市井”释义的单词网站“城市词典”上,对“尴尬”一词排名最高的解释是“你在前往硬币兑换机的路上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如果继续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类比,我们只能在“后台”才能放松下来。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和亲密的朋友及家人在一起时,才终于可以停止表演。我们可以选择中断演出,事实上,我们最好不要一直演戏,没有人喜欢生活在“舞台上”的人。
这就是我们组织社交生活的方式。我们相互配合,构建自己的身份,将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轻快地抛来抛去,就像是演唱会舞台上的气球。如果我们的想法以某种方式被打破,那又怎样?那将造成我们身份的丧失,正如埃德蒙·卡朋特多年前在新几内亚观察到的那样。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想一想,如果我们都在伪装,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是说,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天啊,咱们还是看破不说破好了。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我,那么我为了让你相信我是谁而付出的一切努力还有意义吗?说到这个—我是谁?
我们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旁边蹑手蹑脚地迂回时感到的不安来自我们对被社会排斥的恐惧以及我们称之为“演化残留”的生存本能。在谈论这种本能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它已经失去了用途,好像它只是一种过时的感觉,活跃于我们的蜥蜴脑(lizard brain)中,源自一个被赶出社会团体几乎肯定意味着孤独地死亡的时代。然而,即便今天人们不再受到饥饿的剑齿虎的威胁,被孤立也会带来伤害。当代社会科学统计了社交孤立的潜在危害,发现孤独可以使一个人的死亡风险增加26%——与肥胖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当。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展示能被其他所有人接受的那个自己,难怪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时,感觉是那么可怕。
当我们说类似“我好尴尬!”这样的话时,我认为有时候我们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正感受到日常社交生活可以是多么纠结、混乱。如果你在想要给人留下好印象时紧张起来,也许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感受到了尴尬,而是因为你太真实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远远超过它表面看上去的样子。
对日常生活中的尴尬过于敏感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比起那些迟钝的人,我宁愿做一个意识得到尴尬的人。“有史以来最尴尬文学形象”的竞争者中肯定会有《傲慢与偏见》里的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班纳特的“呆笨又刻板”的追求者。在全书靠前的篇章中有一幕发生在尼日斐花园里的场景,伊丽莎白不得不成为柯林斯先生的舞伴。在接连两支舞中,他都因为“动作错误却不自知”而令她厌烦。他的懵然无知使他的行为显得更加尴尬,就像他那个令人生厌的习惯:定期提醒大家,他与社会地位很高的凯瑟琳·德·布尔夫人关系密切。他就看不出来自己有多么可笑吗?
《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
与柯林斯形成对照的是奥斯汀笔下的另一位追求者:爱德华·费勒斯,《理智与情感》中笨拙却浪漫的主角。“我从无意得罪别人,”他对达什伍德姐妹说,“但我天生腼腆,蠢得可笑,以致常常显得傲慢无礼,其实那时我只是因为天生容易尴尬而畏缩不前。”爱德华很笨拙,但他心里有数。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意图与其他人对这些意图的解读之间存在分歧。这是一种更好的状态,我们将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对此详细介绍。如果意识不到一条鸿沟的存在,你便无法填补它。
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纽约》杂志社公共关系部门兴高采烈地要求编辑人员拍摄新的头像。他们显然更喜欢把我们穿着制服的照片用于公开宣传,而不是用从我们的社交媒体资料中摘取的度假照片。例如,我长时间用于在线会议系统的头像照片,是我在华盛顿州斯诺夸尔米瀑布附近徒步旅行后,穿着亮粉色的耐克连帽衫,头发微卷,对着镜头咧嘴笑着的样子。如果用在推特的个人资料里面,这张照片就足够好了,但它难以精准地彰显我“严肃的专业记者”的身份。
轮到我拍照的那天早晨,我谨慎地挑选了衣服,在发型和妆容上花费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在出门之前,我对着卧室的落地长镜仔细打量着自己,对自己的形象感到非常满意。低调但不失魅力。我把自己捯饬得不错,我想。
然而那天晚些时候,我看到成品照片时,感到非常难堪。我的发型比在镜子里看起来塌扁得多,而且很难看出我脸上带着早上花了那么长时间化的妆(不是那种清爽的“素颜妆”)。后来我向朋友们抱怨自己的照片,并和他们换着看。“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你看起来很漂亮!就和你平常的样子一样。”人们说这样的话,都是为了安慰某个没有安全感的朋友,或者满足一个急需赞美的人,但我听了总觉得有点儿沮丧。你们眼里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自己的照片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根据意如其名的“镜像假设”,你在镜子里的样子确实跟你本人不同,这是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面部感知的大卫·怀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的。他还说,人们往往习惯看自己的镜像,以至于“看到自己左右颠倒会觉得很怪异”。这很适合用来类比,解释我们在自我展示方面付出的最大努力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落空,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无法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想想看,若不借助镜子、照片或者视频,你从没有见过你自己的脸——你真实的面孔——这难道不诡异吗?(在这段确凿无疑的讨论结尾处,大卫使用“那个人”作为一种暗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人”。)
如果你向人们展示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们的镜像,而另一张的左右方向与正常照片的一致(当然,也就是与现实中一致),然后询问他们喜欢哪一张,大多数人会选择镜像,这是他们已经看惯了的形象。你有没有见过自己面部的特写镜头——比方说,你在工作中不得不拍的职业头像——然后注意到你的脸看起来有点儿古怪的不对称?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更喜欢镜像。
但是,如果你让其他人评价照片,他们可能更喜欢非镜像的那张。身为那种认为自己不上相的人,这也许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你的照片不好看,但其他人看不出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是在安慰你,可其实就是在说,是的,你真的就是那样歪着脸招摇过市的。不过,至少他们似乎喜欢你歪着脸的样子。
值得欣慰的是,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确实很善于理解我们的总体声誉,或者是某个群体以整体的形式“看到”我们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能理解他们是如何感知我们的个性的。比如,考虑一下你的工作团队,不是你的每一位同事,而是把所有人看作一个整体,每天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一群人。你认为他们觉得你有多聪明?他们是否觉得你很有趣?体贴?友好?他们发现你的戒备心了吗?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好领导吗?
好消息是,不管你怎么想,你都可能是对的。最近,一篇针对26项有关元准确性(心理学家用于表述对他人想法的准确感知的术语)的研究的综述表明,大多数人都很擅长了解一个群体对他们的总体看法。在一次相关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人员在团队中工作,然后询问每个人对与他们同团队的其他成员的看法,并让他们对每个人的智力、幽默感、体贴程度、戒备心、友善程度和领导能力进行打分。每个接受研究的志愿者还被要求猜测其他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这些品质的。最后发现,人们非常善于猜测团队同伴对自己的看法,准确性甚至超过了用概率预测得到的结果。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自我认知做出这些猜测的,这种自我认知往往确实与整个世界对我们的认知非常吻合,康涅狄格大学研究元准确性的心理学家大卫· A. 肯尼如此解释。“那些认为自己通常会给他人留下坏印象的人确实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肯尼告诉我,“而认为自己会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的人,还就真的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偶尔我参加会议时会把这一点记在心间。如果我感觉我的陈述做得很顺利,那么我可以放心地认为可能就是很顺利。如果我感觉自己砸锅了,那么,至少心里有数总是好事。
然而,我们的个性中有一些方面是别人看得到而我们自己看不到的。2013年的一项研究探索了这些盲点。研究人员首先要求受试人员给自己37种不同的特征和倾向打分,其中包括一些明显的特征,比如懒惰程度和守时程度,但列表中还包括一些对外人来说不太明显的倾向,比如一个人的想象力是丰富还是匮乏,或者他们有多么频繁地感到忧虑。受试者的朋友和家人也收到了问卷,他们也要对其打分。最后,受试者需要猜测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会如何评价自己。
有趣的是,对许多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特征而言,平均来说,受试者们能够准确地预测朋友和家人对他们的评价。他们知道别人认为他们有多么懒惰,他们知道朋友们认为他们迟到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可能不喜欢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但至少他们了解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
不过,对于那些更微妙的特质,比如想象力或者焦虑倾向,结果就不尽然了。例如,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不认为你很有想象力,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他们又看不到你脑海中想象出的缤纷世界,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你的想象告诉任何人的话。或者他们会认为你是稳定和平静的源泉,但实际上你每天晚上都伴着忧虑入睡。这样的特质还有很多,但在这项研究中有两个更值得注意的观察结果:受试者无法准确地估计出,在其他人眼中,他们有多喜欢(或者不喜欢)帮助别人,以及他们有多害怕被拒绝。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时间之前,我和一个朋友进行过一次奇怪的交流。当时她向我发送即时消息,里面有我写的一篇博客的链接,内容是关于孤独的最新研究。“我还没点开就知道是你写的。”她写道,“你总是报道最悲伤的东西。”“哈哈。”我回复道。但我在想:“对不起,什么?”当时我自认为是一个搞笑博主,用我的智慧和学识点亮了人们的生活,可她却觉得我有些扫兴。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看清自己,所以我们依赖别人的视角来填补空白。这触及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的观点:整合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是构建我们的自我意识的途径之一。然而,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间的区别有时是那么明显,以至于透过别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时,会觉得如此难以辨认,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认为别人对你的看法肯定正确,或者至少比你对自己的看法正确,那你肯定是疯了。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并不总是如此。别人对你的看法你无须太当真,但是,改变一下视角,看看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还是值得尝试的,哪怕你看到的东西很伤人。有时候你的好朋友可以扮演你的专属镜子,比如告诉你,你的裤子拉链开了,或者你的鞋上粘着卫生纸。事实上,你会希望能有个好朋友告诉你这些事情,即使当时你会觉得自己很蠢,你也会很高兴他们能如实告诉你。
这些比喻意义上的镜子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而且常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学校里取得的成绩可以是一面镜子,就像工作中的年度绩效考核一样,证明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一直都在接受别人的评价。礼物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以前的一份工作中,我感觉同事们都觉得我年轻、不成熟。某一年,我的老板送我的圣诞节礼物印证了这种印象,那是一本青少年小说,一本很棒的青少年小说—马库斯·苏萨克的《偷书贼》(The Book Thief),我读过这本小说,读得很开心,可解读这份礼物背后的含义却让我不太高兴。
或者考虑一下工资谈判的场景。它就像一面人们用来化妆的放大镜,能让你看清自己的每一个毛孔。你用确凿无疑的数字坦率地说明你认为自己有多大价值,也由此冒着很大的风险—被作为你谈判对象的老板或者招聘经理拒绝的风险。他们也许会告诉你,在公司看来,你的价值要低得多。
2015年,针对这一话题,薪酬对比网站PayScale在用户中开展了一次算不上学术研究的有趣调查。在约3.1万名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曾要求加薪。在那些从未要求加薪的人当中,有约1/3的人承认,这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加薪谈判时的谈话便会感觉很不舒服;另有19%的人害怕别人觉得自己要求过高。
女性和“千禧一代”是在曾经要求加薪的人数中所占比例垫底的两大群体。
或者你还可以想到另一种形式的谈判:“确定关系”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告诉你的约会对象,这就是我认为我对你的价值。在一些定性研究中,社会学家对人们进行深入的访谈,并分析他们的答案,得到的数据表明,一些伴侣完全避开了这些谈话。当采访者问及他们是何事推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促使他们搬到一起住之类的重要里程碑时,很多人都记不清当时做出决定的情形了。“就那么发生了。”他们说。她的租约到期了,他的房租涨了,然后突然之间,两个人就一起逛起了宜家。
2013 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动态,发现那些稀里糊涂地进入像同居或婚姻这样关键的承诺节点的人,在他们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要低于那些曾与伴侣仔细、审慎地谈论对彼此的期望的人——让你忧虑的尴尬谈话往往是物有所值的。
本文节选自
《一旦能放声嘲笑自己,你就自由了》
作者:[美]梅丽莎·达尔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译者:秦鹏
出版年:2021-9-1
编辑 | 仿生沙虫
主编 | 魏冰心